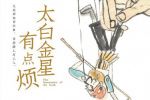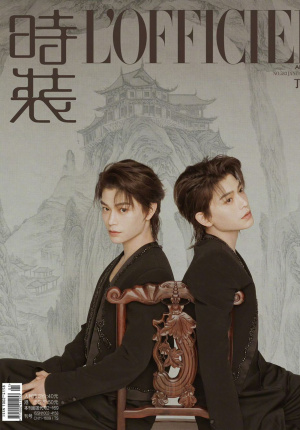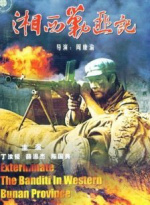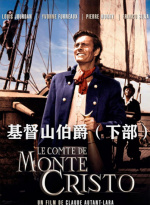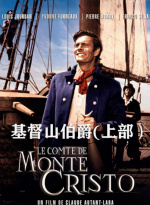我有点欣赏他敢变

在《生吞》确定要拍成影视剧之前,欧豪已经对这本小说爱不释手——
四个人的年少友情、成年后的命运剧变、一个人的自毁式复仇......从情感层面到悬疑层面,哪哪儿都好。
尤其男主角秦理,除了那令人心碎的残酷经历,最击中欧豪的还是他身上单纯干净的特质。
同样,这也是导演张晓波定下欧豪的原因:
一开始就发现他有一双特别纯粹的眼睛,这个特别像秦理的眼神。
美梦成真般地,欧豪成了秦理。
与一个较真格的剧组一起,交出了今年最生猛刺痛的悬疑剧——《胆小鬼》。

老实说,很多人,包括我,一开始都无法把欧豪和瘦弱天才秦理联系到一起。
因为在大银幕上看过他太多阳光、血性的一面。
当欧豪大胆走出舒适圈,惊喜发生了。
十年前,自行车后座的秦理,第一次与黄姝四目相对。
都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冲自己笑,他就躲在王頔的背后,兀自欢喜起来。
冬日暖阳下,磁带里唱着《胆小鬼》,一场暗恋正在发芽。
满满的少年气,看得人忍不住嘴角上扬。

但这并不是什么天才和神女的青春爱恋。
他们一个是“杀人犯的儿子”,一个是“精神病的女儿”,被外界的凌辱声推到一起,直到成为黑暗中照亮彼此的那把火炬。
黄姝的陨落,带走了秦理世界里的最后一点光亮。

十年后,修车厂打工的秦理,戴着助听器沉默不语,半边脸布满骇人伤疤。
老板挑衅,他反手就飞去一个铁扳手。
眼神里的寒意,与东北的铁锈和冰雪融为一体。
当一个人对世界毫无畏惧,也说明他对世界毫无希望和眷恋。

只一个转场,我们便看到命运在一个人身上碾压过的痕迹。
看到这,我突然明白欧豪为什么可以拿下这个角色,他那处于男孩和男人之间的半熟气质,与秦理的前后转变恰好契合。
两个时期的反差,就像欧豪形容的那样——
十年前秦理是个活人,十年后他是个“死”人。虽然人活着,但他的心已经“死”掉了。

长大后的秦理已经“死”了,除了他想念黄姝的时候。
过度的思念有时会把黄姝带回秦理身边,她还像以前那样天真烂漫地分享生活琐事,他还像以前那样沉溺地微笑倾听。
直到她问:“你一个人,还好吗?”秦理顿时嗓子发干,几乎要哭出声来。
但她又说,“我喜欢看你笑”。秦理不知如何是好,哭和笑的表情纠结在一起。
幻象的短暂温存和大梦初醒的剧痛,狠狠撕扯着他的心。
也对着我的心脏,猛揪了一把。

除此之外,欧豪的几次哭戏,都深深地打到了我。
不管是独自把爷爷送去医院,听到父亲枪毙前念给自己的信,还是在学校遭受暴力屈辱......


他越是克制,越是能让我们与秦理的艰难和脆弱共情。
随着内心的隐隐作痛,我必须承认:
秦理这个角色,欧豪接住了。
从最初的投缘,到后面的投入,欧豪确实像导演张晓波说的那样:
表演完成度非常高,你越往后看,你会越对他的表演有认同感。
追剧已过大半,与欧豪时隔两年后再次对话,我感受到某种蜕变正在他的身上发生
——
戏内,我们看到了秦理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;
戏外 ,我们也看到了欧豪作为演员的蜕变。
这个蜕变不是突然开窍,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,而是伴随着质疑,伴随着沉淀,一步步打磨出来的表演质感。
非科班出身的欧豪,拥有与同龄人不太一样的成长轨迹。
16岁就开始自力更生,边打工边读书,送外卖、卖衣服、做超市导购。

那些被烟火熏染过的年少经历,让他更懂人情、知珍惜,也让他始终扎根在生活里,对表演有自己的理解与领悟。
《左耳》上映后,“张漾”有了脸。
回过头来看,欧豪在这部电影中的表演显得稚嫩、笨拙。
但,恰恰是不藏拙,让一个外表玩世不恭、内心孤傲叛逆的二次元常见人设,有了更真实的痛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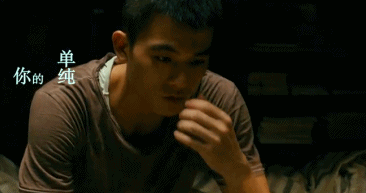
我第一次将欧豪与“演员”二字绑定,是因为电影《少年》。
他饰演一个在校园霸凌阴影下成长,人生被撕裂的少年。
一边,是遍体鳞伤仍不肯退一步的硬骨头;一边,是与恋人擦肩只敢留刹那温存的软肋。
悸动与绝望交织中,一个复杂又有后劲儿的角色变得鲜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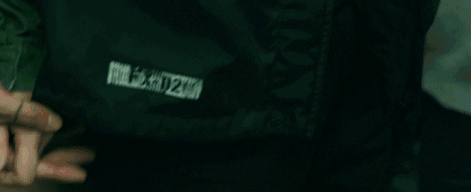
不乖,够狠。
——这大概是导演们看中欧豪的特别之处,也是他留给大银幕最初的痕迹。
就连演校园戏,也是最能打的那一个。
但很快,《铤而走险》再见——
狠依然狠,表演质感却变了。很明显,有了厚度。
学生气、少年气全数褪去。圆寸短到贴头皮,眼神里多一层凛冽的邪性。
微微下压的枪管对准人的脑门时,如同一头困兽,扑面而来的冷血与暴戾。
只有面对唯一在乎的哥哥时,被逼到绝境的他,才显露出濒临疯狂的外放情绪。

算一算那年欧豪也才27岁。
已经抹去了大众对他“小鲜肉”的直白印象,却也在《建军大业》《烈火英雄》《中国机长》等主旋律电影里,贴上了一张新的“硬汉”标签。
大概本人骨子里就属“拼命三郎”,演狠人的要诀是对自己更狠。
不谙水性,却敢下海拍动作戏;拍山路飙车追逐战,坚持不用替身自己上,亲身体验了车头冲出悬崖命悬一线的恐惧;拍打斗肉搏更别提了,摸爬滚打留几块伤疤是家常便饭……
比起技巧,他的表演更倚仗感受与体验,因此,以真演真成了打动观众最“笨”也最奏效的方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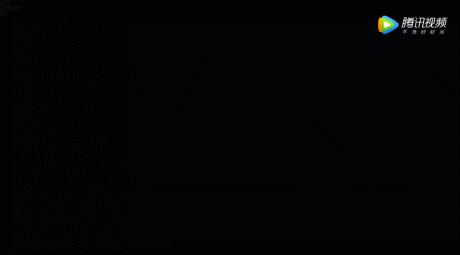

这种能引起共振的表演冲击力,在《八佰》里达到了高潮。
欧豪饰演的端午,是一个出身湖北农村的孩子。和弟弟加入保安团,只为了“看一看上海”,混口饭吃。
短短四天内,端午经历了炮火的轰炸,亲人的离世,战友一个接一个牺牲……
还没准备好长大,已经被迫迎接世界最残酷的一面,他的蜕变可想而知。
而要演出这种蜕变,欧豪必须成为端午。
每天走进一比一还原搭建的四行仓库,他慢慢扫过墙上的弹孔、防御的沙袋,感受自己将要经历的一切。有时候还会一个人蹲在“地牢”找状态,透过小小的窗口看向对岸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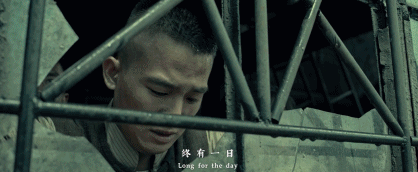
那种“上一秒带着幻想憧憬,下一秒心突然就收紧”的代入感,慢慢扎进了他的心里。
最后,我们看到了一个从惧怕、茫然、连为什么要开枪杀人都不懂的男孩,变成了一个奋不顾身冲锋陷阵的男人。
欧豪陪端午“生”了一次,“死”了一次。
《八佰》首映式上,他自己也看哭了。

从不会演戏的业余感,到以情动人的感染力,欧豪离好演员越来越近。
这种进步还有一个更显性的证据——台词。
演《左耳》时,欧豪还带着浓重的“胡建”口音。
到了《建军大业》,虽然有时候仍会前后鼻音不分,但是口音已经几乎听不出来。
《八佰》里为了演好端午,他特意学习湖北方言,拍摄期间一直学、一直练,为的是让语言成为一种本能。
直至现在,我们突然发现欧豪的原声台词已经超过一大批科班小生。
咬字清晰,断句准确,字正腔圆的发音演北方人也毫不违和。

作为演员,欧豪谈不上天赋派。
但他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,敢于正视短板,然后一声不吭地夯实自己,补足自己。
从不走捷径,也从不急于辩解——
“批评的声音你也得去消化,看他们说的点跟内容是否是自己做得不足、还需要自己继续努力的。其实好的声音跟其他不一样的声音在我的成长路上来说都非常重要,有鼓励有鞭策,才能够时刻提醒自己更努力地去做好自己的事情。”
作为观众,最欣慰的也莫过于此——
一个演员一步一个脚印地,终于磨出了身上的光芒和质地。
快快戳视频看专访,感受欧豪的蜕变
推 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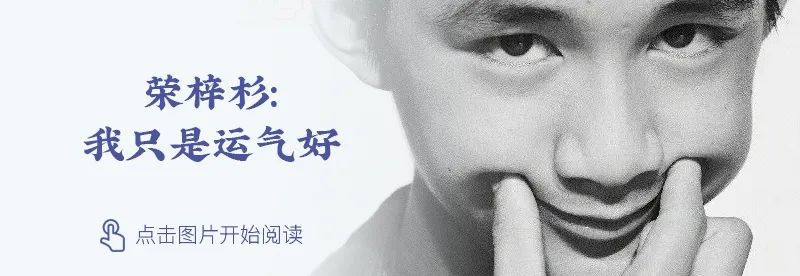

点“在看”,未来可期!↘↘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