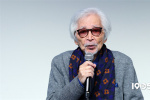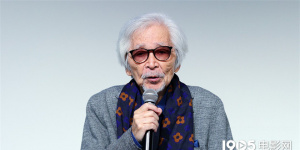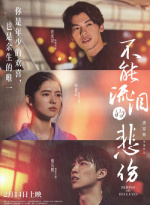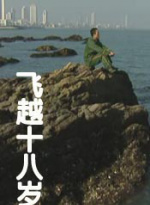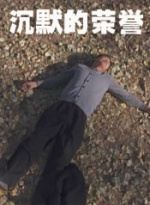出道30年,她第一次这样亲手揭开伤疤!
1905电影网专稿 25年前,舒淇在电影《千禧曼波》中饰演都市女孩Vicky。影片开场,她行走在基隆陆桥,甩动长发、大步前行,不时回眸的神情中,交织着迷离、叛逆,与对未来的隐约渴望。
正是从《千禧曼波》起,舒淇遇到了她艺术生涯的伯乐——侯孝贤导演,由此从香港类型电影跨越至作者艺术片的世界,绽放异彩。此后,她凭借《最好的时光》摘得最佳女主角奖,通过《刺客聂隐娘》闪耀国际影坛,并连续受邀担任欧洲三大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,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电影舞台。

当年那座基隆陆桥,定格了舒淇青春中最动人的一瞬,也引领她跨过千禧年,奔向更加耀眼的新世纪。如今,这座桥因电影而得名“曼波桥”。舒淇,带着她的第一部导演电影《女孩》,再次回到这里,架起摄影机,完成了从演员到导演的身份跨越。
《女孩》的故事创作灵感来自舒淇的童年经历,影片中的女孩名为林小丽,生活在80年代末的基隆港,有一个酗酒家暴的父亲,一个时常责骂她的母亲,在迷惘与压抑中长大。她的成长轨迹,也悄然触动了母亲内心未曾愈合的创伤。

在侯孝贤导演的鼓励下,舒淇鼓起勇气第一次动笔撰写剧本,《女孩》的写作历经十年,反复打磨、几易其稿。最终,电影不仅顺利完成,更接连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与多伦多国际电影节,并斩获釜山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导演奖。
今年正值舒淇入行三十年,也迎来丰收之年。舒淇说:“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,这也和我的生活观有关系,我特别快乐,懂得感恩,身边有好多贵人帮助我。”
从演员到导演,舒淇将三十年来所积累的生命体验和艺术能量,都倾注到《女孩》之中。此前,她已经接受多家媒体采访,分享了诸多幕后故事。在我们这次短暂的对话中,决定换个角度,从影片里的两处点睛之笔——“曼波桥”和“红气球”为切口走进这部电影,重新认识舒淇。

1905电影网《对话》栏目专访舒淇
曼波桥的联结
《女孩》的故事在曼波桥开启,也在此走向结局。这座桥不仅是地理坐标,更是一个承载宿命与选择的视觉场景。它是母女命运的时空交叉点,既联结着她们相似的原生家庭困境,也预示着她们不同的生命路径。
拍摄前,舒淇一直在寻找一条能够承担双重隐喻的路:母亲与女儿争吵后,女儿出走,母亲追寻,两人在不同时间于同一地点交汇——女孩勇敢向前,走向未来;母亲转身拐入岔路,仿佛陷入漩涡,难以脱困。
勘景时,舒淇意外重遇《千禧曼波》的陆桥。她发现,这座桥的结构恰好能够实现她心中的视觉叙事。“我没有想到会这么神奇,当时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它既能让我联结到侯导,也可以为电影联结到一个非常好的收尾。”
舒淇注意到,如今的曼波桥加装了铁网,与当年拍摄《千禧曼波》时有所不同。“铁网已经生锈,带着一种我想表达的那个年代特有的铁锈般的味道。而且桥就在铁网里,所以我把它设计成女孩每天上学的必经通道,就像她被困在笼子里。而十多年后,她已经在网外,在网球场上去过另一种人生了。”

林小丽与母亲之间,是一种互为镜像却又彼此伤害的关系。母亲自己尚未真正长大,却被迫成为母亲。童年的阴影、丈夫的暴力、生活的重压,层层笼罩着她。她爱女儿,却不知如何表达,只能沿用自己从小承受的方式去对待林小丽。
而林小丽面对严厉的母亲,内心并没有真正的恐惧与怨恨,她更多是希望带着母亲一起逃离父亲。母亲饰演者汤毓绮9m88这样形容:她们像两条互相拉扯的线。女儿在旁边时,母亲觉得好烦;可一旦放手,母亲又仿佛失去了自己。

舒淇也并未将林小丽的父亲彻底塑造成一个脸谱符号化的男性形象。他在家里是施暴者,在外是“好好先生”,一度想戒酒,尝试回归正常生活。
舒淇分享了其中的细节设计:他回到家打开冰箱,习惯性想拿一瓶啤酒,但他没有,换成了水;有一天天还没黑他就回家了,看见桌上还有女人未做完的加工活,还顺手帮忙做一点。当他准备要改变自己的时候,却又受到刺激,瞬间变回原形,向女人施暴,出去喝酒、发泄。
故事写到这里,走向舒淇原先设想的结局——男人醉酒驾车出车祸,同时女人将女孩送离这个家。

“我想留下一个悬念:他到底死了没有?小丽还需要被送走吗?”舒淇透露,制片人叶如芬和剪辑指导张叔平在看过结局后建议她改写,他们认为应该给观众一个情绪出口。
关于新的结局,舒淇构思了许久。她在书桌前静坐六小时,思考如何为这个故事写下更圆满的收笔。忽然,舒淇想到自己那个总爱说“反话”的母亲。“她从不正面回答我,从不会告诉我她心里真正的想法。我想把这一点写进结尾。”
于是,我们看见十多年后,长大成人的林小丽回到家中,与母亲重逢。时过境迁,她质问母亲为何当年没有保护好她,为何连一句“对不起”都不曾说。母亲却认为,女儿如今过得好就好了,为何不能体谅她的不易。
这些代际之间的隔膜、难以言说的伤痛,正是许多中国式母女关系的缩影,都浓缩在这个不是和解的无言结局里。

说到这,舒淇提起一件关于她母亲的往事:“在拍《回魂计》时,我母亲来探班,刚好在拍一场我被老公狠狠毒打的戏。她在旁边看,我的发型师跟她说:‘阿姨,这场戏你女儿被打了不要看。’结果我妈回答:‘我小时候打得比这更狠。’”
这是一种很典型的自我保护反应。舒淇把这视为母亲“独特”的生活哲学,用幽默掩饰真实感受,用盾牌阻挡真实想法。话语间,舒淇流露出对母亲的理解,也有一丝无奈。
红气球的幻想
“晚上8点多,整个城市寂静了许多,隐隐约约摩托车的声音从远而近,小丽突然绷紧了神经,自己手忙脚乱地躲进旁边的衣柜里......母女三人一起待在房间里,等着外面的男人消气。”
这段剧本情节,来自舒淇对童年的真实记忆。“为了躲避我爸喝醉酒回来,可能会打我,我小时候常常躲在衣柜里。”为保护小演员,电影没有直接呈现女孩挨打的画面,而是通过声音与意象的强化,传递父亲所带来的暴力。
“在衣柜里,我的听觉会特别灵敏,我爸踢到塑料瓶或铁罐的声音,我都听得出来。所以我希望这场戏的音效,能营造出环绕感。在黑暗里,女孩听到所有声音的细节,恐惧不断上升——直到那只手伸过来,就代表她已经被殴打了一顿。”

舒淇回忆道:“我小时候曾梦到被纸娃娃掐,醒来后照镜子,发现自己脖子上真的有三个小红点。”她将《女孩》定义为“奇幻写实电影”,除了父亲那只手的阴影意象,片中还融入了很多来自她童年幻想与梦境的元素,为林小丽构筑出一个虚实交织的内心世界。
例如,林小丽透过学校墙上的破洞,望见了年轻时的妈妈;她偷吃面包时,远处有一只乌鸦静静注视;她走在妹妹身后,看见妹妹的书包里突然飘出一只红气球。
红气球的意象巧妙而富有诗意。它既是对侯孝贤《红气球之旅》的致敬,也象征着林小丽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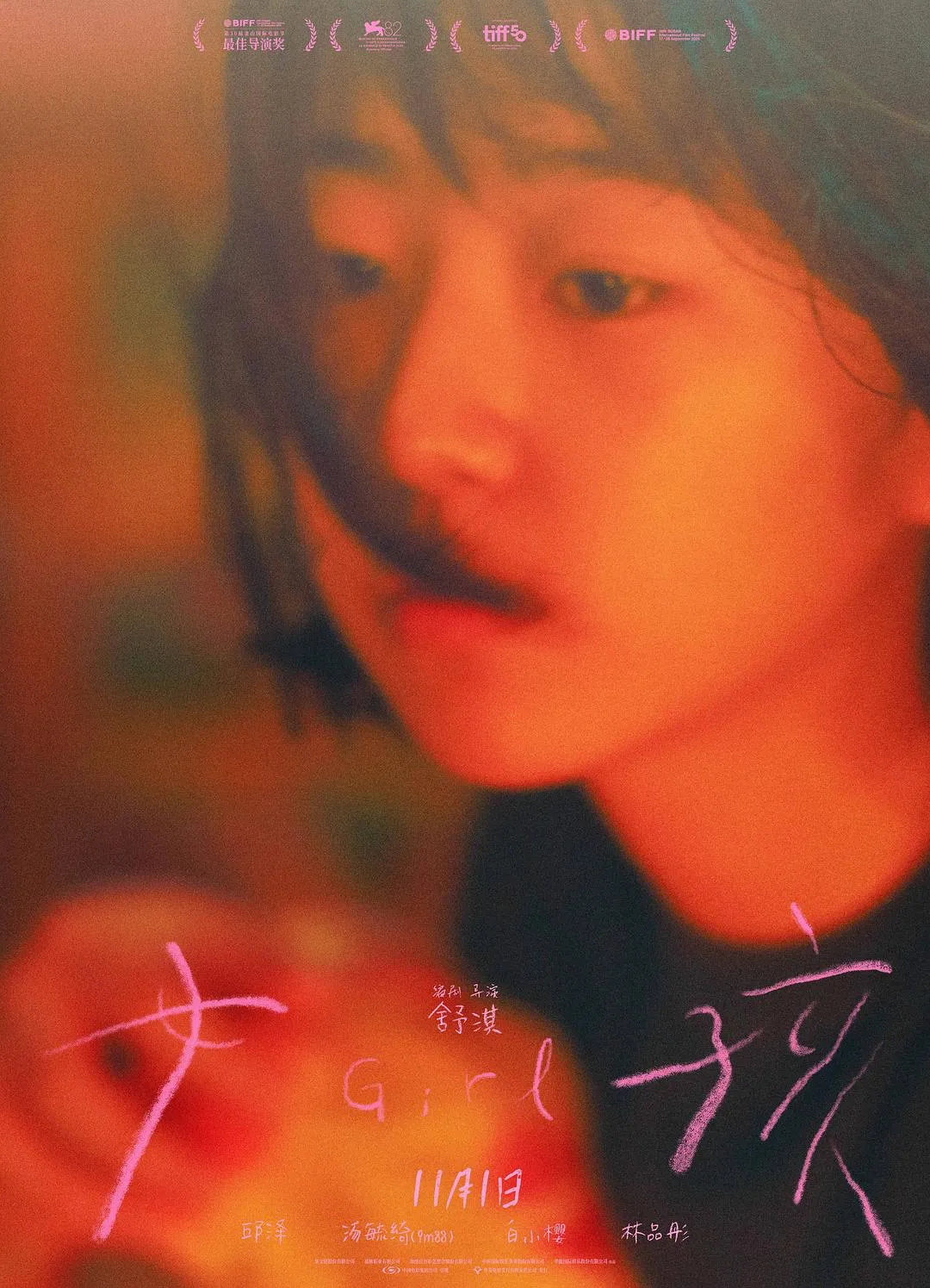
林小丽是一个不爱笑的女孩,同学林莉莉说她“连笑起来都那么苦”。这与爱笑的妹妹形成鲜明对比。“长期在压抑环境中长大的孩子,脸上会有一种苦相,一种孤独感。选角时,我看到白小樱有很深的黑眼圈和眼袋,看起来就像从来没睡好过的女孩,于是选择了她。我再从她的个性出发,去完整塑造林小丽。”
尽管林小丽的人物形象有着舒淇本人的写照,但她强调自己与角色的性格截然不同,她从小都会想尽办法让自己快乐、忘记悲伤。“哪怕我被揍得伤痕累累,哪怕我出车祸,我都可以在痛苦中找到欢笑声。我是一个可以让自己快乐的人,否则可能早就崩溃了。”
小时候,舒淇会偷拿妈妈的一块钱去买糖果。“一块钱可以买十颗糖,一颗颗慢慢吃,那一刻是特别快乐的。”长大后,她读到一本书《秘密》,学会吸引力法则的精髓:“如果一直感到痛苦,就会很痛苦。可是如果我一直秉持正能量和希望,总有一天,好运就会降临到我头上。”

在舒淇出道第三十年,她的转身和《女孩》的诞生,收获掌声、鲜花和奖杯,好运都不是偶然,而是她选择勇敢的必然。这样一个回溯、解剖自我深处创伤的历程,并非如舒淇预期的“疗愈”,反而更多的是痛苦,“就像曾经的伤口又被挖开了”。
舒淇坦言,对有过相似经历的观众而言,看这部电影或许是“残忍”的。她仍然希望《女孩》能提醒每一位父母:以正确的方式向孩子表达爱。身体上的伤痕或许会愈合,但心里的创伤不会轻易消失,会留下难以抹去的疤痕。
从当年躲在衣柜里的女孩,到站在曼波桥上执掌电影的导演,舒淇将自己对成长最切身的感受和体悟,都装进了《女孩》,随着那只红气球——载着伤痛与希望,飘过时光,最终抵达属于她的、自由的天空。
[1905电影网]独家原创稿件,未经授权不得转载,违者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